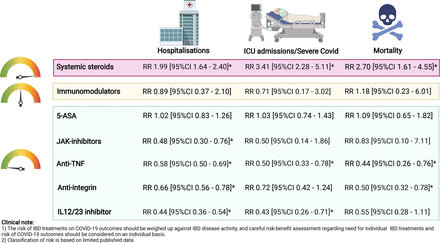条文本
摘要
COVID-19大流行引发了相当大的担忧,即炎症性肠病(IBD)患者,特别是接受免疫抑制疗法的患者,可能会增加获得SARS-CoV-2的风险,在COVID-19后预后更差,与普通人群相比,疫苗反应不佳。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总结了关于COVID-19风险和相关结局的数据,以及关于IBD患者使用SARS-CoV-2疫苗的最新指南。新出现的证据表明,用于IBD的常用药物,如皮质类固醇(而非生物制剂)与COVID-19的不良结果有关。重新诊断或延迟诊断IBD的风险没有增加,但是,在大流行期间,内窥镜检查程序的总体减少导致内窥镜检查漏检的癌症数量增加。IBD药物对疫苗反应的影响已成为最近的研究重点。数据表明,与未接受抗肿瘤坏死因子(TNF)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抗肿瘤坏死因子(TNF)药物治疗的IBD患者对SARS-CoV-2疫苗的体液反应减弱,抗体衰减更快。令人欣慰的是,无论IBD治疗方法如何,所有接种疫苗的患者的突破性感染和住院率仍然很低。国际指南建议,所有接受免疫抑制疗法治疗的IBD患者应在其治疗周期的任何时间接受三剂SARS-CoV-2疫苗,并尽快接受进一步的加强剂量。未来的研究应集中于我们对生物治疗患者抗体衰减率的了解,哪些患者需要额外剂量的SARS-CoV-2疫苗,COVID-19对IBD病程和活动性的长期风险,以及长期COVID-19对IBD患者的潜在风险。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溃疡性结肠炎
- 克罗恩氏病
- 免疫反应
- 炎症性肠病
- SARS-CoV-2
- 疫苗
- 抗体
这是一篇开放获取的文章,根据创作共用署名非商业(CC BY-NC 4.0)许可证发布,该许可证允许其他人以非商业方式分发、混音、改编、在此基础上进行构建,并以不同的条款许可其衍生作品,前提是正确引用原始作品,给予适当的荣誉,任何更改都已注明,并且使用是非商业性的。看到的: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数据来自Altmetric.com
关键信息
与普通人群相比,炎症性肠病(IBD)患者感染COVID-19的风险没有增加,并且结果基本相似,包括住院、重症监护住院和死亡率。
IBD患者COVID-19不良结局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合并症数量增加、皮质类固醇使用和IBD活性增加。
未感染COVID-19的经生物治疗的IBD患者应继续使用大流行前的IBD治疗,不应选择性地更换。
没有证据表明重新诊断或延迟诊断IBD的风险增加,然而,大流行期间内窥镜检查程序的总体减少导致内窥镜检查漏检的癌症数量增加。
应鼓励IBD患者在其治疗周期的任何时间接受完整的SARS-CoV-2疫苗疗程,并告知在接受全身皮质类固醇、抗肿瘤坏死因子单药或联合治疗以及Janus激酶抑制剂时,疫苗反应可能会减弱。
对于接受多种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患者,可能需要更强化的免疫策略,然而,报告多种SARS-CoV-2疫苗剂量后疫苗反应的数据正在等待,并将为未来的政策建议提供信息。
简介
截至2022年2月,全球有超过4.2亿例病例和580万例死亡与COVID-19有关,这是由SARS-CoV-2引起的。1 2由于Delta (B.1.617.2)和Omicron (B.1.1.529)等新变种的出现,大流行仍然是对全球健康的持续威胁,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抗体中和。3 4严重感染COVID-19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和潜在的医学共病,如心血管或代谢性疾病。5
炎症性肠病(IBD)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UC)是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IMIDs),在全球发病率迅速上升。6COVID-19的发病机制与IBD在分子水平上存在潜在的交叉。ACE2和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 (TMPRSS2)的上皮表达似乎是SARS-CoV-2病毒进入宿主肠细胞的必要条件,从而导致无对抗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途径导致急性肺损伤。7在患有肠道炎症并经常使用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IBD患者中,ACE2的上皮表达将保持不变甚至下调,8 - 10这可能会影响COVID-19的疾病谱及其临床管理。
患有IBD的患者出现严重感染和肺炎的风险更高,11 - 13特别是那些使用生物药物治疗的患者,已知它们与机会性感染的风险增加有关。14在大流行开始时,人们担心IBD患者是否会出现更糟糕的健康结果。也不确定使用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患者是否像以前在其他疫苗可预防感染中所证明的那样,降低了疫苗反应。15—直到最近,包括IBD在内的IMIDs患者还被排除在SARS-CoV-2疫苗临床开发计划之外。自从新型疫苗平台在国际上推出以来,其中许多疫苗此前从未在IBD患者中进行过研究,因此出现了许多关于在这些患者中接种SARS-CoV-2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在本综述中,我们旨在全面综述COVID-19和IBD管理的最新证据,特别是COVID-19在IBD患者中的风险和结果,IBD药物对COVID-19结果风险的影响,COVID-19是否影响IBD疾病活动性,以及SARS-CoV-2疫苗在IBD患者中的新数据和指导,为当前的临床实践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IBD对COVID-19的影响
IBD患者感染COVID-19的风险
自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人们担心IBD和其他与免疫失调相关的疾病患者感染SARS-CoV-2的风险可能会增加。在大流行早期的两项意大利小型研究中,IBD患者的COVID-19血清流行率很高,19与普通人群相比,他们感染SARS-CoV-2的风险可能更高。20 21然而,随后意大利的一项单中心研究报告了相互矛盾的结果,20.来自西班牙的区域病例系列表明,IBD患者的COVID-19调整后发病率(0.74)低于普通人群。22美国的两项大型登记研究证实,IBD患者中COVID-19的总体发病率较低(0.23%),与无IBD患者相似。23来自美国的一些数据甚至表明,与非IBD患者相比,IBD患者感染COVID-19的风险更低(风险比(RR) 0.79, 95% CI 0.72至0.86),然而,这可能是由所谓的“屏蔽”现象解释的,因为一些政府建议IBD患者呆在家里,尽量减少面对面接触,这些患者被认为患有严重COVID-19的风险更高。24在整个欧洲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在丹麦的一项队列研究中,IBD患者的患病率低于普通人群(2.5% vs 3.7%, p<0.01)。25在全球范围内,截至2022年初,IBD患者中报告的COVID-19患病率为0%至5.95%。24-29
在一项包括17项研究的荟萃分析中,每1000名IBD患者的合并发病率为4.02,而普通人群的合并发病率为6.59。IBD患者的合并相对风险没有显著增加(RR 0.47, 95% CI 0.18至1.26),IBD亚型之间没有显著差异。30.尽管最初存在担忧,但IBD患者的SARS-CoV-2感染率似乎与普通人群相当。
高龄已被证明是与IBD中COVID-19发展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但尚未确定风险增加的年龄界限。30 31尽管人们最初担心免疫抑制对SARS-CoV-2获得的影响,但使用生物药物与COVID-19发展风险增加并无关联。28 30 32
COVID-19对IBD患者的预后
在大流行期间,研究排除冠状病毒监测流行病学(SECURE-IBD)国际登记帮助临床医生和患者更好地了解COVID-19在IBD患者中的结果。在2022年1月登记关闭之前,报告了来自74个国家的7038例COVID-19病例,以确定IBD治疗方案对COVID-19结局的影响,包括住院和重症COVID-19,定义为重症监护病房(ICU)入院、机械通气和死亡的综合。33-38在整个大流行期间,SECURE-IBD一直是IBD社区的一个信息量巨大的资源,然而,在队列的代表性方面存在重大限制,部分原因是在注册性质上次于医生主导的选择。尽管是一个全球注册表,但来自美国的病例占数据库的三分之一以上,限制了数据集发现对其他人群的普遍性。此外,接受非生物治疗的患者代表性不足,因为近三分之二的病例接受了抗肿瘤坏死因子(抗tnf)、抗整合素或IL12/23抑制剂的治疗。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SECURE-IBD仍是迄今为止评估IBD治疗对COVID-19预后影响的最大队列研究。
IBD患者的COVID-19常见症状与一般人群相似。大部份病人出现发烧(67.5%)及咳嗽(59.6%),约四分之一病人出现腹泻、嗅觉丧失或呼吸困难,约10%病人出现肠胃不适,包括腹痛、恶心或呕吐。39IBD患者胃肠道表现的比例较高,但在COVID-19期间可能被活动性疾病所混淆。40
住院治疗
尽管与一般人群相比,IBD患者与covid -19相关的住院率略高,但住院患者的临床病程与非住院患者相似。在大流行早期进行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报告称,IBD患者的住院风险没有增加(RR 1.10, 95% CI 0.74至1.40)。40相反,来自荷兰和美国的两项大规模研究报告,IBD患者的发病率更高,为17%-68%。24小时41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住院患者的临床病程与未住院患者相似,这反映了入院门槛在各国之间的差异。在大流行后期获得的IBD患者数据估计在欧洲为21%,在拉丁美洲为66%。22日使在对全球11项研究的一项荟萃分析中,COVID-19的合并住院率为28%。30.最近,在英国范围内的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中,超过1700万人,包括2万多人接受免疫抑制药物治疗(OpenSAFELY),即使在控制年龄、性别和共病后,IBD患者住院的风险仍然增加。46然而,尽管这些数据是从英国40%的全科实践中提取的,但没有捕捉到某些混杂因素,包括可能降低感染风险的屏蔽状态和偏向于null的结果。此外,由于很难在该数据集中确定活动性IBD和SARS-CoV-2感染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可能存在对暴露状态进行错误分类的风险。
与covid -19相关住院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活动性IBD和存在≥1种非IBD共病,如心血管疾病。42 43 47这些危险因素的影响在SECURE-IBD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其中IBD患者的住院率从儿童和年轻人(10-19岁)的5%到老年人(> - 80岁)的47%不等。有三种以上共病的患者的发病率(60%)高于没有共病的患者(9%),33与克罗恩病患者相比(RR 1.55),30.西班牙裔和黑人患者与白人患者相比(RR 2.5-3.6)。48
重症监护、机械通气和肾脏替代治疗
尽管最初的数据表明,在大流行期间,IBD患者可能增加了重症监护入院人数,增加了机械通气的需求,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比例与普通人群相似。在SECURE-IBD中,IBD患者的ICU入院率为3%,在一项国际荟萃分析中为5.3%。30.与一般人群相比,IBD患者入住ICU的风险相似(RR 0.85, 95% CI 0.69 ~ 1.06)。24在另一项来自荷兰的基于人群的研究中,IBD患者的ICU入院率与普通人群相似(12.5% vs 15.7%)。41OpenSAFELY研究表明,IBD患者入住ICU和/或死亡的风险略有增加(HR 1.08, 95% CI 1.01 - 1.16)。46在SECURE-IBD注册表中,总体机械通气率为2%,在老年患者中增加到9%。33IBD患者与非IBD患者机械通气的相对风险相似(6.3% vs 11.2%, p=1.00),41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的风险(RR 1.00, 95% CI 0.84 ~ 1.19)和需要肾脏替代治疗的风险(RR 1.00, 95% CI 0.60 ~ 1.66)。24
死亡率
初步数据表明,IBD患者的病死率可能很高,从0%到33.3%不等。20 22 41-45随着更细致的数据的出现,这一比例大大降低了;在一项荟萃分析中,合并COVID-19的IBD患者的汇总死亡率为4.3%,与普通人群的死亡率相似。30.SECURE-IBD患者的总死亡率为2%,老年患者(20%)明显高于年轻患者(0%)。33进一步的研究证实,IBD患者和非IBD患者的COVID-19死亡率相似(RR 0.95, 95% CI 0.71至1.26),然而,按疾病亚型分层的研究报告称,UC患者的死亡率可能高于克罗恩病(RR 1.94, 95% CI 1.22至3.10)。24 30SECURE-IBD的多变量分析表明,这种关联可能被年龄、性别、吸烟状况和共病所混淆。34 49 50
与不良临床结局(包括ICU入院、机械通气和/或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出现呼吸困难、活动性IBD、存在≥1种共病和使用全身类固醇。24 25 34 42-45 47 51一个经过验证的预后模型用于预测IBD合并COVID-19患者的不良结果,在对已知危险因素(包括年龄、男性性别、共病、皮质类固醇和生物使用)进行调整后,显示出出色的区分能力,住院曲线下面积为0.79,ICU入院曲线下面积为0.88,死亡曲线下面积为0.94。50
IBD药物对COVID-19预后的影响
全身性类固醇
在整个大流行期间,有大量证据表明全身类固醇对发展为COVID-19的IBD患者的临床结果具有不利影响。然而,大多数已发表的数据都受到IBD活动、COVID-19严重程度和伴随类固醇使用之间未测量的混淆的影响。尽管如此,数据仍然具有说服力和可复制性,并有助于在IBD急性治疗中定位皮质类固醇。在决定停止全身性皮质类固醇的情况下,谨慎减少剂量对避免阿狄森危机的风险仍然很重要,特别是在并发疾病的情况下。52
在SECURE-IBD注册表中,33皮质类固醇的使用与6.9倍的严重COVID-19风险和11.6倍的COVID-19死亡风险独立相关。33 34这一发现在一项涵盖北加州440万健康计划成员的大型回顾性队列中得到了重复,其中一些人患有IBD,其中在SARS-CoV-2感染之前使用口服强的松是随后住院、ICU住院和死亡的一致风险因素。53进一步的研究还证实,皮质类固醇的使用与SARS-CoV-2感染风险增加、住院和重症监护需求增加有关。24 54 55在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中,与未接受类固醇治疗的患者相比,类固醇治疗患者的合并相对住院风险(RR 1.99, 95% CI 1.64至2.40)、ICU住院风险(RR 3.41, 95% CI 2.28至5.11)和死亡率(RR 2.70, 95% CI 1.61至4.55)均显著高于未接受类固醇治疗的患者。30.
5-aminosalicylic酸
关于5-氨基水杨酸(5-ASA)对IBD患者COVID-19病程的影响,已有相互矛盾的结果报道。大流行早期进行的几项研究(包括两项荟萃分析)表明,与未接受5-ASA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5-ASA治疗的患者重症监护、呼吸机使用和死亡的风险增加。34 35 56例如,在接受5-ASA治疗的患者中,合并相对风险为住院1.59 (95% CI 1.39至1.82),ICU入院2.38 (95% CI 1.26至4.48),死亡率2.62 (95% CI 1.67至4.11)。30.然而,在最近的一项大倾向评分匹配队列研究中,未发现5-ASA与不良结局或死亡风险增加相关。24随着SECURE-IBD的更多数据出现,与该组织最初的报告相反,34在后来的出版物中,5-ASA不再与任何不良临床结果、住院或死亡相关(RR为1.02,95% CI为0.83至1.26),这可能反映了最初的相关性是由于报道偏倚造成的,包括5-ASA和柳氮磺胺治疗患者中未报告的轻度COVID-19病例,以及生物治疗患者中轻度COVID-19病例比例过高,或协变量未完全控制。36
免疫调制剂
根据美国和法国开展的两项基于人群的研究,与treatment-naïve IBD患者相比,使用传统免疫调节剂,即硫嘌呤和甲氨蝶呤,与COVID-19风险增加(RR 0.89, 95% CI 0.33至2.44)、住院(RR 0.94, 95% CI 0.66至1.35)、机械通气或死亡(RR 0.35, 95% CI 0.09至1.43)无关。57 58在接受免疫调节剂治疗和未接受免疫调节剂治疗的患者中,ICU入院和死亡率的合并相对风险相似。30.在SECURE-IBD中,甲氨蝶呤而非硫嘌呤被报道与住院和死亡风险轻微增加相关(RR为1.26,95% CI为1.00至1.57),但与严重的COVID-19或死亡无关。36值得注意的是,与单独使用生物制剂相比,硫嘌呤单一疗法或与生物制剂联合使用也与发生严重COVID-19的风险更高相关。35
生物药物
大约四分之一的IBD患者接受生物药物治疗,最初,这些疗法对COVID-19的影响尚不确定。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大流行的演变和新数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物制剂对IBD患者是安全的(图1)。
IBD治疗对COVID-19结果的影响。使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计算相对风险,比较每种药物类别与未使用该药物治疗的COVID-19的结果。ICU入院包括由ICU入院、机械通气和非COVID-19死亡组成的复合结局。指标上的颜色代表IBD药物对COVID-19结果的集体风险:绿色=低风险,琥珀色=中等风险,红色=高风险。*表示95% CI未超过1的显著结果。用参考数据创建的图。30 36使用BioRender.com。5-ASA, 5-氨基水杨酸;IBD,炎症性肠病;ICU,重症监护室;JAK-inhibitor, Janus激酶抑制剂;RR,相对风险;肿瘤坏死因子。
Anti-TNF药物
使用TNF拮抗剂(IBD患者最常用的生物制剂)与COVID-19风险增加无关。57此外,与未接受抗tnf治疗的患者相比,抗tnf治疗的患者在ICU入院、机械通气或死亡的风险没有增加34在美国、法国和丹麦的三个基于人群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24 25 58
一些研究表明,在接受生物治疗的患者中,发生严重COVID-19的风险可能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这些药物在抑制COVID-19相关炎症并发症基础上的细胞因子炎症途径方面的作用。30 56 59在一项荟萃分析中,与使用其他非生物制剂治疗IBD的患者相比,使用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的合并相对住院风险(RR 0.34, 95% CI 0.19至0.61)、ICU住院风险(RR 0.49, 95% CI 0.33至0.72)和死亡率(RR 0.22, 95% CI 0.13至0.38)较低。30.一项荟萃分析还发现,与皮质类固醇或5-ASA相比,接受抗tnf治疗的患者住院和ICU入院的风险降低。56
然而,接受抗tnf治疗并联合免疫调节剂的患者出现COVID-19不良结局的风险增加。尽管法国一项全国性研究发现,接受抗tnf单一治疗的患者与接受抗tnf联合治疗的患者的住院死亡率相似,58SECURE-IBD数据显示,接受抗tnf联合治疗的患者发生严重COVID-19的风险高于接受抗tnf单一治疗的患者(8.8% vs 2.2%, RR 4.01, 95% CI 1.65 ~ 9.78)。35在来自三个由不同imid患者组成的国际注册中心的汇总分析中,抗tnf单药治疗似乎比其他常用治疗方案(包括抗tnf联合治疗)具有最佳的安全性。60
Anti-integrins
抗整合素vedolizumab对COVID-19结果影响的数据一直存在矛盾。一份报告显示,与单独使用5-ASA治疗的患者相比,vedolizumab治疗与发生COVID-19的风险增加相关(RR 1.70, 95% CI 1.16至2.48)。54SECURE-IBD的初步数据也表明,与抗tnf治疗的患者相比,vedolizumab的住院风险增加(RR 1.39;95% CI 1.001至1.90),但无严重COVID-19风险。37 54
在SECURE-IBD的最新数据中,发现与未接受维多单抗治疗的患者相比,维多单抗治疗与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相关(RR 0.66, 95% CI 0.56至0.78),且与严重COVID-19风险无关。36与接受其他IBD药物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维多单抗治疗的患者患COVID-19的风险可能更高,部分原因是抗整合素不仅与肠道中的效应记忆细胞结合,还与上呼吸道结合。61 62更有可能的是,最初的数据不足以检测使用不同IBD药物治疗的患者之间的真正差异。随着在大流行期间使用较不常用处方药(如维多单抗)治疗的患者的数据不断丰富,COVID-19不良结局风险的增加消失了。
抗白介素12/23剂
虽然我们对ustekinumab(一种白介素12/23抑制剂)治疗患者的风险了解仍然有限,但在security - ibd中,与未使用ustekinumab治疗的患者相比,使用ustekinumab与较低的住院或死亡风险相关(RR 0.44, 95% CI 0.36至0.54)。36总体而言,目前的证据强调,与抗tnf相比,韦多单抗治疗(RR 0.85, 95% CI 0.56至1.28)和ustekinumab治疗(RR 1.25, 95% CI 0.56至2.80)患者发生严重COVID-19的风险尚不可知,36在接受不同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中,住院的相对风险相似。58
Janus激酶抑制剂
Tofacitinib是一种Janus激酶抑制剂(JAKi),已被批准用于治疗UC,与血栓形成和感染,特别是带状疱疹的高风险相关。63关于其在COVID-19期间安全性的现有数据有限。在SECURE-IBD的亚组分析中,仅包括37例托法替尼治疗的IBD患者,与其他治疗方案相比,使用托法替尼与住院、ICU住院、机械通气或死亡风险增加无关。38没有血栓事件的报道。然而,在美国最近一项针对包括IBD在内的大量IMIDs患者的社区研究中,31%接受JAKi治疗的患者与接受其他生物制剂治疗的患者相比,出现严重COVID-19的风险增加(RR 3.35)。53令人欣慰的是,最近的数据显示,托法替尼与较低的住院和死亡风险相关(RR 0.48, 95% CI 0.30 ~ 0.76)。36托法替尼也被证明是降低COVID-19死亡或呼吸衰竭风险的有效治疗方法。64
COVID-19对IBD的影响
COVID-19对IBD疾病活动的影响
很少有研究评估COVID-19对ibd相关疾病病程、活动和恶化的影响,特别是对接受免疫调节剂的患者的影响。大多数病例系列或回顾性队列受到样本量小和对疾病活动性混杂因素调整不足的限制。在美国的一项队列研究中,118例发生covid -19的IBD患者(62%为克罗恩病,55%为生物治疗)在covid -19后随访了6个月。65略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报告了与COVID-19相关的胃肠道症状,但这可能与近三分之二的队列在COVID-19发病前后出现活动性IBD症状这一事实相混淆。令人欣慰的是,在covid -19前后,疾病活动性、内窥镜评估或实验室标志物没有显著变化。
在美国40家医疗机构的855458名患者的回顾性倾向评分匹配队列研究中,评估了实验室确认的SARS-CoV-2感染后发生IBD暴发的风险和重新发生IBD的风险。24SARS-CoV-2检测阴性的患者作为对照。4310例有COVID-19病史的IBD患者中,5.3%和6.8%的IBD症状分别在1个月和3个月内突然发作。与生物疗法无显著相关性。在3个月的随访中,有COVID-19病史的患者发生ibd相关疾病发作的可能性是没有COVID-19病史的患者的1.3倍(95% CI 1.18至1.51)。这些观察结果可能是由于SARS-CoV-2的肠道感染,和/或回肠和结肠组织中ACE2的上调导致疾病爆发。66 67在该队列中,774例(0.1%)患者在COVID-19后再次诊断为IBD,与没有COVID-19病史的对照组相比(RR 0.55)。原因尚不清楚,但当分析仅限于COVID-19后至少6个月的诊断时,结果仍然显著。
IBD患者长COVID-19的风险
最近的证据表明,急性SARS-CoV-2感染后持续症状可持续数周。这种情况被称为长时间COVID-19或急性后COVID-19综合征,涉及呼吸、心血管、神经、胃肠和肌肉骨骼系统等多个器官。68常见症状包括疲劳、肌痛、呼吸困难、心肌损伤、认知障碍和睡眠障碍。69不同地区的研究报告了不同的长COVID-19发病率,60天的发病率从33%到87%不等70 716个月或更长时间,35%到76%。72 73意大利的一项小型研究报告了急性SARS-CoV-2感染后康复的IBD患者长COVID-19的临床特征。74患病率为39.6%,三分之二的患者表现为虚弱,三分之一的患者表现为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嗅觉丧失、老年痴呆、记忆丧失、皮肤症状、肌痛,少数患者表现为持续性呼吸困难或抑郁。
出现长COVID-19的IBD患者更多为女性,而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没有长COVID-19症状的患者没有差异。74长COVID-19的确切发病机制仍不清楚,但COVID-19后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可能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因为基线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已被证明可以预测长COVID-19的风险。75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感染新变种的sars - cov -2,预计发展为长型COVID-19的IBD患者数量将大幅增加。需要进一步研究COVID-19的发病机制及其对IBD患者的长期影响。
COVID-19大流行期间IBD的管理
关于COVID-19大流行期间IBD患者管理的国际和国家指南与大流行前的实践建议密切一致,特别是在尽量减少全身皮质类固醇使用方面。尽管这些建议主要基于专家意见,但随着新数据的出现,临床建议也会定期更新。76 - 82随着全球多次COVID-19浪潮期间积累的新数据,认为IBD患者可能受到COVID-19的不利影响,相反,COVID-19可能恶化IBD相关疾病活动的观点已在很大程度上减弱。概述了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开展研究和制定指南的经验教训箱1.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吸取的教训
优化资源和基础设施
利用现有的研究基础设施,如当地和国际上积极从事研究的临床医生和护士组成的特定疾病网络。在2019冠状病毒病期间,这使研究问题得到优先排序,使多个国家的病例记录表格标准化,并提高了数据质量,加强了数据和实践建议。
安全的在线数据库,如研究电子数据采集(REDCap),允许快速建立研究和监测登记,包括电子同意书。考虑征得同意,以允许与基于社区和医院的国家记录数据库建立数据联系,并使患者可被召回。
患者和公众参与
如果需要面对面的研究访问,应尽量减少临床医生和患者接触的时间以降低感染风险,并尽量减少常规医院输液预约期间的样本收集时间。例如,如果当地资源允许,可以考虑通过邮政刺指血液检测试剂盒进行远程采样。
利用通讯、在线视频和其他面向患者的材料,最大限度地参与研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个人层面的研究结果反馈给患者以保持动机,特别是纵向研究。
适应性和进化的研究问题
定期审查研究目的和目标,以解决大流行演变过程中的初步和长期结果,例如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疫苗开发和长期COVID-19的风险。
数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COVID-19大流行早期发布数据有助于发现我们在理解方面的直接差距。考虑通过在线登记或仪表板实时发布特定研究的数据,并以实时系统综述的形式正式发布数据,从而在大流行期间丰富数据并对其进行荟萃分析。
已知诊断为IBD的患者
大多数国际组织建议,确诊为IBD的患者应继续使用大流行前的IBD治疗,该治疗成功地诱导和维持了缓解。新诊断为IBD的患者,或已确诊诊断并正在经历症状发作的患者,应根据大流行前的护理标准进行管理。这些措施包括继续使用免疫调节剂、生物制剂、JAKi,并考虑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皮质类固醇治疗的使用,以及开始新开始的皮下治疗以尽量减少医院就诊次数。
在大流行之初,患者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在医院接受维持生物治疗时,提出了有关医院感染SARS-CoV-2的风险以及就医对医疗资源的影响的担忧。83例如,在生物制剂之间切换,从静脉注射英夫利昔单抗到皮下注射阿达木单抗,大多数针对IBD患者的指南都不推荐76 78不像那些针对风湿病患者的药物。84 85部分原因是,在使用第一种生物制剂获得缓解后,使用第二种生物制剂重新获得疾病缓解的时间较短,更有可能与抗药物抗体的发展有关,从而限制了IBD未来的治疗方案。86 - 88在一些法域,已经有一些成功的大流行相关项目报告了在IBD患者中选择相同分子的替代给药途径,特别是从静脉注射英夫利昔单抗到皮下注射英夫利昔单抗(CT-P13)。89 90
急性重症UC患者的新表现
考虑到疾病的严重程度、可能需要的免疫抑制程度以及在医院发生COVID-19的风险,对新诊断为急性严重溃疡性结肠炎(ASUC)的患者进行管理尤其值得关注。两个总部位于英国的RAND适宜性小组支持现有的建议,特别是在这两名儿童中开始皮质类固醇治疗,升级到英夫利昔单抗和及时的手术干预,无论COVID-19状态如何91和成人92与炎症性肠病。
在PROTECT-ASUC研究中,一项覆盖英国60家急性二级护理医院的病例对照研究,招募了782例ASUC患者(398例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384例历史对照组),与历史队列相比,更多的患者在大流行期间接受了抢救治疗或手术(55% vs 42%, p<0.001),大流行期间抢救治疗的时间更短。93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与历史队列相比,大流行中更多地使用生物制剂、环孢素或托法替尼的抢救和初次诱导疗法;两组的结肠切除术率相似。尽管在大流行期间,与历史对照组相比,更多地使用以门诊为基础的途径进行静脉注射类固醇,但大多数患者仍作为住院患者进行管理。94虽然病例数量较少,但在作为住院患者治疗的个体和作为门诊患者治疗的两个队列中,结肠切除术的发生率是相当的。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医疗保健提供者应继续调整以医院为基础的治疗途径,以改善对新诊断的IBD患者的护理,同时限制他们感染SARS-CoV-2的风险。95
IBD患者和COVID-19诊断
对一名SARS-CoV-2检测呈阳性的IBD患者(无论有无症状)的管理仍存在争议。专家们一致建议对确诊COVID-19的患者修改IBD治疗方法。(图2)76 77 96指南的一般原则包括考虑逐渐减少口服皮质类固醇或改用布地奈德,同时使用硫嘌呤、甲氨蝶呤和托法替尼,并将生物治疗推迟2周直到康复。然而,这些建议大多仅基于共识,并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最新数据单独考虑。虽然类固醇一直被认为是严重COVID-19的风险因素,但类固醇在管理COVID-19住院患者方面已被证实的益处表明,对于因COVID-19住院的IBD患者,不应总是停用类固醇。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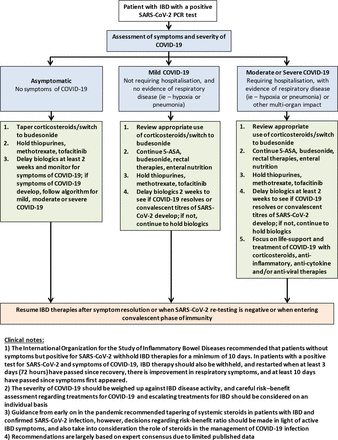
感染COVID-19的IBD患者的治疗考虑。改编自最新的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和美国胃肠病协会指南。76 775-ASA, 5-氨基水杨酸;IBD,炎症性肠病。
国际炎症性肠病研究组织建议,没有症状但SARS-CoV-2阳性的患者至少10天不接受IBD治疗。96对于SARS-CoV-2检测呈阳性并有COVID-19症状的患者,也应停止IBD治疗,并在康复至少3天(72小时)后重新开始治疗,呼吸道症状有改善,且自首次出现症状至少10天后重新开始治疗。
弱势群体
患有IBD的儿童
与成人一样,接受免疫抑制的IBD儿童被认为是脆弱的,并且COVID-19发生不良后果的风险可能更高。98令人欣慰的是,与患有IBD的成年人相比,他们没有更高的COVID-19发病率或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99 - 101与成人相比,儿童(包括IBD患者)的COVID-19病程较轻,儿童对COVID-19的不良后果较少。99与成人一样,建议对新诊断或经历疾病爆发的儿童进行大流行前治疗,91 102因为在这一年龄组中,COVID-19期间的治疗延迟与疾病爆发有关。103长期监测对于更好地了解儿科IBD与新发现的covid -19后病毒综合征(称为多系统炎症综合征)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104尤其是那些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人。105 106
患有IBD的孕妇
同样,患有IBD的孕妇接受免疫抑制是COVID-19发生不良结局风险的一个担忧。107然而,在整个大流行期间,该队列尚未显示出较高的COVID-19发病率或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与妊娠相关的不良结局也很少发生。100 108有限的研究报告了IBD和COVID-19患者的妊娠结局。109 110在第一种情况下,110一名在妊娠早期出现急性ASUC的妇女随后被检测为SARS-CoV-2阳性并发生自然流产。这一结果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可能与UC的严重恶化、COVID-19的影响、遗传异常或上述因素的组合有关。在第二种情况下,109一名患有轻度IBD症状的妇女在怀孕18周时患上了COVID-19。她有轻微的COVID-19症状,在COVID-19期间暂时停用阿达木单抗后,妊娠没有受到影响。在244名IBD孕妇(75%接受生物治疗)的回顾性队列中,仅报告了一例COVID-19病例。108迄今为止,患有IBD的孕妇的SARS-CoV-2感染风险或不良结局似乎没有升高,但要得出更明确的结论,还需要更大的现实世界队列。
IBD患者的内窥镜检查和疾病监测
在大流行早期,大多数指南都建议推迟IBD患者的常规或选择性内窥镜检查,111 - 115除新诊断(中重度指数高)的高危人群外,因疾病发作、肠梗阻或硬化性胆管炎入院者除外。116 - 120建议在进行COVID-19检测前仔细对患者进行分类,适当使用个人防护装备,由内窥镜工作人员重新处理内窥镜和附件。此外,在大流行高峰期间,首选使用粪便钙保护素和成像(MRI、CT或超声)的微创评估和监测方法。一项对英国全国内窥镜数据库的分析发现,大流行期间的内窥镜检查程序减少到大流行前正常水平的80%-95%,每周内窥镜检测到的癌症数量减少了58%,漏诊癌症的比例从19%(胰胆管)到72%(结直肠)不等。121在美国也观察到类似的趋势,结直肠癌的诊断率降低了约50%。122与ibd相关的程序、调查和医院就诊的新兴数据继续显示,与大流行前相比,大流行期间这些活动的数量有所减少。123 124
随着各国从最近一波COVID-19疫情中恢复过来,国家指南根据当地需求和资源优先考虑了大流行后获得内窥镜检查服务。125 - 128英国已经发布了更新的指南,根据内窥镜检查的指征和时间对患者进行分层。例如,对于间隔小于3年的患者,在原预产期后6个月内进行监测结肠镜检查;对于间隔3年或以上的患者,在原预产期后12个月内进行内窥镜检查。129
在大流行期间,实施家庭生物疗法输液以减少住院人数。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缺乏资源或适当的监测,协调护理的工作人员也很少,试图建立这种服务是具有挑战性的。130基于家庭的治疗药物监测生物药物和抗药物抗体,患者使用手指穿刺进行小容量毛细管内血液取样,发现相当于在医院或诊所进行常规静脉穿刺。131这个以家庭为基础,病人为主导的创新132 133是远程医疗的一种潜在有用的辅助手段,并可能促进安全的IBD管理,同时保护患者免受SARS-CoV-2感染。130 134
SARS-CoV-2疫苗接种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引入减少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住院和死亡人数。它们具有良好的耐受性,据报道,与一般人群相比,IBD患者接种疫苗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似,疾病恶化的风险没有增加。135 - 137然而,先前的研究表明,肺炎球菌感染后疫苗反应受损15日18在接受英夫利昔单抗治疗的患者中接种流感疫苗,而不是vedolizumab138或ustekinumab。139因此,人们最初担心,服用免疫抑制药物的患者对SARS-CoV-2疫苗的免疫反应可能减弱,对SARS-CoV-2感染的免疫保护能力较弱。大多数已发表的数据集中于对BNT162b2、mRNA-1273和ChAdOx1 nCoV-19疫苗的疫苗应答,因为这些疫苗在世界范围内最常使用。保护的最佳相关性,定义为保护个人免受疾病侵袭所需的免疫反应,140对SARS-CoV-2感染的影响仍有待确定。因此,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的替代品已被用于预测疫苗的疗效。这些方法包括中和抗体分析,141刺突(S)蛋白受体结合域(anti-S RBD)的抗体作为中和抗体的相关因素,142以及T细胞研究作为细胞免疫的衡量标准。
SARS-CoV-2疫苗接种的体液反应
多项研究报告了两剂mRNA (BNT162b2, mRNA-1273)或腺病毒载体(ChAdOx1 nCoV-19)疫苗后的高血清转换率,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IBD患者中,转换率从81%到100%不等(图3)。143 - 146在最近一项对9000多名IBD患者的荟萃分析中,合并的血清转化率为0.96 (95% CI为0.94至0.97)。147在纳入的31项研究中,在第二剂SARS-CoV-2疫苗后的28-179天内确定了血清转换率。疫苗剂量和患者采样间隔的差异,使用不同的抗体测定,以及复制抗体阈值以定义血清转化的困难,使得不同研究中IBD患者接种疫苗后血清转化率的解释和背景化具有挑战性。
炎症性肠病(IBD)治疗对SARS-CoV-2疫苗反应的影响GMR尖刺抗体浓度由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计算,该模型比较了每种药物类别与健康对照组的尖刺(S)抗体反应的大小。GMR被认为相当于抗体的折叠变化。红色阴影框代表IBD药物与减毒疫苗反应。根据参考数据创建的图。137 143-146 154 175使用BioRender.com。anti-TNF,抗肿瘤坏死因子;5-ASA, 5-氨基水杨酸;GMR,几何平均比;jak抑制剂,Janus激酶抑制剂。
SARS-CoV-2疫苗的细胞介导免疫反应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也可能有助于独立于体液反应的对SARS-CoV-2感染的保护性免疫。两种非免疫损害的研究148 149和免疫功能不全的150队列研究表明,强大的T细胞反应与SARS-CoV-2感染的更好结果相关。体液免疫和T细胞免疫的解耦在非免疫功能低下的个体中也有报道,151如果T细胞反应没有受损,这可能与体液反应减弱的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直接相关。虽然IBD患者的数据有限,但初步研究令人放心。coral -IBD发现,303名接受一系列治疗的IBD患者的抗s RBD抗体浓度与对SARS-CoV-2疫苗的T细胞克隆反应之间相关性较差,尽管他们发现,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抗tnf治疗的IBD患者的T细胞克隆深度增强。152CLARITY IBD研究是一项英国范围内的IBD患者前瞻性队列研究,旨在调查英夫利昔单抗和韦多珠单抗和/或伴随免疫调节剂对IBD患者SARS-CoV-2获得、疾病和免疫的影响,报告了抗s RBD抗体和抗spike T细胞反应的解偶联,然而,在英夫利昔单抗和韦多珠单抗治疗的患者中,在一到两剂疫苗后,观察到相似的T细胞反应。146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这些发现,并确定T细胞疫苗反应对IBD患者SARS-CoV-2免疫的相对贡献。
IBD药物和疫苗反应
接受抗TNF治疗的患者
尽管接种疫苗后血清转换率高,但与其他生物疗法相比,在接受抗tnf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SARS-CoV-2抗spike (S)抗体浓度较低。在CLARITY IBD中,使用两剂BNT162b2或ChAdOx1 nCoV-19疫苗后,2279例英夫利昔单抗治疗患者的几何平均值(几何SD)抗sars - cov - 2s抗体水平显著低于1031例韦多单抗治疗患者(BNT162b2(英夫利昔单抗566.7 U/mL vs vedolizumab 4555.3 U/mL)和ChAdOx1 nCoV-19(英夫利昔单抗184.7 U/mL vs vedolizumab 784.0 U/mL)疫苗)。146同时使用免疫调节剂治疗的患者的抗sars - cov -2抗体浓度也较低。这种关联后来在以色列的一项前瞻性对照多中心研究RECOVER中得到了证实。137比较了73例健康对照、67例抗tnf治疗和118例非抗tnf治疗的IBD患者在接种两剂BNT162b2疫苗后的抗体反应。接种第二剂疫苗四周后,抗tnf治疗的个体与健康对照组相比,SARS-CoV-2抗s IgG的几何平均浓度显著降低。在本研究中,在评估中和抗体和使用SARS-CoV-2尖刺假颗粒中和试验时,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在RECOVER研究中,抗tnf注射时间和抗tnf药物水平均与接种后SARS-CoV-2抗s浓度无关,这表明SARS-CoV-2疫苗可在抗tnf治疗周期的任何时间注射。
接受非抗TNF治疗的患者
关于接受其他生物和非tnf免疫抑制疗法治疗的IBD患者对SARS-CoV-2疫苗的抗体反应是否也减弱的数据继续出现。大多数研究对其他生物疗法的患者都显示了令人放心的结果,但受到每种药物类别的小样本量的限制。在602例IBD患者(292例(48.3%)抗tnf治疗,112例(18.6%)vedolizumab治疗,91例(15.1%)ustekinumab治疗,51例(8.5%)巯基嘌呤治疗和36例(6.0%)5- asa治疗)的单中心队列研究中,将第二剂量BNT162b2、CX-024414或ChAdOx1 nCoV-19疫苗后的抗体反应与168名健康对照组进行了比较。153IBD患者和对照组的疫苗后血清阳性率相似,抗tnf治疗患者和非抗tnf治疗患者抗sars - cov -2 IgG中位水平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每组患者数量有限和所使用的测定方法不同。
来自英国的VIP研究评估了362例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IBD患者(78例(12.4%)硫嘌呤治疗,72例(19.9%)英夫利昔单抗/硫嘌呤治疗,63例(17.4%)英夫利昔单抗治疗,62例(17.1%)维多单抗治疗,57例(15.7%)ustekinumab治疗和30例(8.3%)托法替尼治疗)和121例健康对照组在接种BNT162b2或ChAdOx1 nCoV-19疫苗后的抗sars - cov -2 S蛋白抗体反应。154与对照组相比,使用英夫利昔单抗、英夫利昔单抗/巯基嘌呤和托法替尼治疗的患者抗sars - cov -2 S蛋白抗体的几何平均值显著降低(英夫利昔单抗:156.8 U/mL(几何SD 5.7);p<0.0001,英夫利昔单抗/硫嘌呤:111.1 U/mL(5·7);p<0·0001,托法替尼:429·5 U/mL(3·1);p=0·0012,对照:1578.3 U/mL(3.7))。相比之下,preventive - covid研究比较了317例接受一系列生物和非生物治疗的IBD患者的抗体反应,仅发现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的患者在接受两剂量mRNA疫苗(BNT162b2, mRNA-1273)后抗体反应减弱,而其他药物类别则没有。144在这项探索性分析中无法进行正式的假设检验,因为只有13例患者正在接受布地奈德治疗。
在其他患有IMIDs的患者队列中,包括牛皮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肾脏异常患者,也观察到在接种mRNA COVID-19疫苗后抗体反应降低,这并不令人惊讶。155对5360名患者(其中一些患者患有IBD)进行的系统综述的多因素荟萃回归显示,使用抗cd20而非抗tnf (p=0.058)的治疗与两剂量mRNA疫苗接种后SARS-CoV-2抗体浓度降低相关。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不同的样本量、疾病包含、药物使用和抗体检测所解释的,有待进一步的数据来证实这些发现。
最近,在一项涉及111名IMIDs患者的多中心研究中,与健康对照组相比,使用1-磷酸鞘氨酰氨(S1P)调节剂治疗的患者在接种SARS-CoV-2疫苗后血清转换率较低。156虽然这些患者使用S1P调节剂治疗多发性硬化症,但最近,一种S1P抑制剂ozanimod已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用于治疗UC。在使用ozanimod治疗的IBD患者中是否也会观察到减毒血清转换率仍有待确定。
既往有SARS-CoV-2感染史和不同疫苗类型的患者
之前感染SARS-CoV-2对抗体浓度和血清转化的影响,在完全接种疫苗后,在健康患者中显示出类似的影响方向,157没有IBD的患者接受免疫抑制疗法,158IBD患者。据报道,无论治疗级别如何,既往感染过SARS-CoV-2的患者在单剂或两剂疫苗接种前抗SARS-CoV-2抗体浓度和血清转换率较高。146 153 159与ChAdOx1 nCoV-19相比,BNT162b2疫苗接种与IBD患者更高的抗体反应相关,无论治疗方法如何。146 15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尚不清楚使用巯基嘌呤与接受ChAdOx1 nCoV-19疫苗的个体抗SARS-CoV-2抗体浓度较低有关,但基于mrna的SARS-CoV-2疫苗后抗体反应峰值较高,因此建议将其用于免疫抑制队列。
持久性、疫苗有效性和突破性感染
在非免疫抑制队列中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诱导的SARS-CoV-2抗体会衰减,141 160 161可能会导致疫苗效力降低,随后有突破性感染SARS-CoV-2的风险。162因此,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中,对SARS-CoV-2疫苗的血清学反应受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这些患者的持久性和随后的疫苗有效性。在这方面,CLARITY IBD在接受两剂量BNT162b2(英夫利昔单抗:26.8天(95% CI 26.2至27.5)vs vedolizumab: 47.6 (95% CI 45.5至49.8)和ChAdOx1 nCoV-19(英夫利昔单抗:35.9天(95% CI 34.9至36.8)vs vedolizumab: 58.0天(95% CI 55.0至61.3)p<0.0001)疫苗治疗的患者中表现出较短的抗体半衰期(95% CI 55.0至61.3)。146将抗tnf治疗患者的抗体半衰期与其他非抗tnf治疗(包括ustekinumab, 5-ASA和布地奈德以及维多单抗)进行比较(38天vs 74天,p=0.045),也观察到类似的结果。163相反,在接受生物和非生物治疗的IBD患者中,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报告,在接种两剂基于mrna的疫苗(BNT162b2, mRNA-1273)后,疫苗有效性为80.4%,164与最初的疫苗试验相似。165 166在这个大型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IBD队列中,大多数患者(54.8%,8048/14,697)仅接受5-ASA治疗,研究是在主要循环变异为alpha (B1.1.7)时进行的。
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IBD患者中,突破性感染的发生率尚不清楚。尽管CLARITY IBD报告英夫利昔单抗治疗组比韦dolizumab治疗组有更多的突破性感染(5.8% (201/3441)vs 3.9% (66/1682), p=0.0039),且SARS-CoV-2 PCR阳性的时间更短,146这一发现尚未在其他研究中观察到。
另外两项队列研究发现,接种两剂疫苗后,突破性感染率没有差异。167 168以色列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评估了12109名IBD患者,他们接受了两剂BNT162b2疫苗。167作者报告,与未接受抗tnf或皮质类固醇治疗的IBD患者相比,接受抗tnf或皮质类固醇治疗的患者的突破性感染率或SARS-CoV-2 PCR阳性的时间没有差异(0.4% vs 0.3%, p=1.0)。同样,在美国一项大型回顾性队列研究中,IBD患者与非IBD对照组之间的突破性感染没有差异(0.36% vs 0.28%, RR 1.3 (95% CI 0.83 ~ 2.05))。168总的来说,无论IBD治疗方法如何,只有不到1%的突破性感染患者需要住院治疗。136 146
应谨慎解释突破性感染率的差异,因为各研究之间的差异结果可能是由研究期间疫苗类型、给药间隔、SARS-CoV-2流行率和显性变异发病率的差异来解释的。
第三剂量和变种的关注
2021年11月26日,世卫组织将SARS-CoV-2的omicron变种B.1.1.529指定为值得关注的变种。169由于其传播性增加和人群免疫力下降,欧米克隆变体正在推动大量的突破和SARS-CoV-2再感染,据估计,SARS-CoV-2疫苗接种后的血清学反应需要比以前的SARS-CoV-2变体大40倍才能实现保护性免疫。170由于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早于欧米克隆和更新的SARS-CoV-2变体的出现,171关于大多数国家建议IBD患者接受第三剂或加强剂SARS-CoV-2疫苗后抗体反应的数据很少发表。
来自HERCULES队列的初步数据是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非随机研究,评估了85例接受第三剂SARS-CoV-2 mRNA疫苗的IBD患者的血清学反应。172他们发现所有的患者都是血清阳性,并且在第三次剂量后,中位抗体浓度比两次剂量系列后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接受皮质类固醇、抗tnf、单一或联合治疗的患者的SARS-CoV-2抗刺突IgG抗体浓度明显低于未接受这些治疗的患者(中位数38 (IQR 20-120) vs 73 (IQR 58-167), p=0.015)。在一项涉及495名IBD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其中皮质类固醇的使用与第三剂SARS-CoV-2疫苗后SARS-CoV-2刺突蛋白抗体降低相关(折叠变化:0.07(95%可信区间0.02至0.20))。173
迄今为止,尚无关于IBD患者接种第四剂疫苗的结果和疗效的数据。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建议,免疫功能中度或严重受损的12岁及以上人群,包括那些正在接受高剂量皮质类固醇或其他可能抑制免疫反应的药物积极治疗的人,总共应该接种4剂SARS-CoV-2疫苗。这四剂疫苗由三剂mRNA SARS-CoV-2疫苗的主要系列以及一剂mRNA SARS-CoV-2疫苗的增强剂组成。174然而,第四剂疫苗对体液或细胞免疫反应的有效性以及药物如何影响随后的抗体衰变仍不清楚。
结论
总之,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IBD患者发生COVID-19的风险没有增加,感染COVID-19后重新发生IBD的风险也没有增加。然而,年龄较大、合并症增多和全身使用皮质类固醇是IBD患者COVID-19术后不良结局的危险因素。研究表明,COVID-19对IBD疾病活动没有短期影响,但需要在更多更大的队列中进行验证,且长COVID-19的风险尚不清楚。皮质类固醇的使用似乎与COVID-19不良结局的风险增加有关,但用于治疗IBD的大多数其他药物,包括生物制剂、美沙拉嗪和柳氮柳嗪,与COVID-19严重结局无关。有一些信号表明,抗tnf疗法可能发挥保护作用。这些结果支持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保持IBD患者服用最佳治疗IBD的药物。
接种SARS-CoV-2疫苗的风险较低,强烈建议IBD患者接种SARS-CoV-2疫苗,但在一些IBD患者中,特别是服用抗tnf药物的患者中,对SARS-CoV-2疫苗的保护性免疫反应减弱。接受抗tnf +免疫调节剂联合疗法和JAKi治疗的患者对SARS-CoV-2疫苗接种的抗体反应也较差,这使他们面临感染SARS-CoV-2的潜在风险增加。这些发现支持为IBD患者安排疫苗剂量的个性化方法。未来的研究应探索与疫苗犹豫相关的因素及其在IBD群体中的影响,免疫抑制对疫苗疗效的长期影响,以及寻找疫苗成功的预测生物标志物,以及第四剂疫苗的时间。关于长期结果和血清学反应降低机制的进一步数据也是必要的。
伦理语句
患者发表同意书
参考文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脚注
NAK和SCN是联合资深作者。
推特@SimengLin, @LouisHSLau, @nchanchlani1, @DrNickKennedy, @Siew_C_Ng
SL、LHL和NC的贡献相当。
贡献者SL, LL和NC构思概念并起草手稿。NAK和SCN构思了概念,并对手稿进行了批判性的修改。所有作者都同意了手稿的最终版本。
资金SL由惠康GW4-CAT奖学金支持。NC感谢英国克罗恩&结肠炎协会的支持。SCN的部分资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的InnoHK,政府提供。
相互竞争的利益SL报告了来自辉瑞公司的非财务支持,来自Ferring公司的非财务支持,在提交的工作之外。LL没有利益冲突需要申报。NC没有利益冲突需要声明。NAK报告了来自F. Hoffmann-La Roche AG的资助,来自Biogen的资助,来自Celltrion Healthcare的资助,来自Galapagos NV的资助,来自Immundiagnostik的非财政支持,来自AbbVie的资助和非财政支持,来自Celltrion的资助和个人费用,来自Janssen的个人费用和非财政支持,来自武田的个人费用,来自Falk博士的个人费用和非财政支持,在提交的工作之外。SCN曾担任杨森、艾伯维、武田、费林、Tilotts、Menarini、辉瑞的演讲者,并在提交的工作之外获得了奥林巴斯、费林、杨森和艾伯维的研究资助。
出处和同行评审委托;外部同行评审。